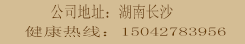那年菊花开
文/张晓凝
一
秀站在河水里,在一块齐腰的大青石上,拼命搓洗一条发白的牛仔裤,确切地说,那是一件男式牛仔裤,“怂人,把裤子穿成啥哩!”她对着污黑的洗衣粉沫子嗔骂。
春日的阳光,细碎地洒在河面,折射在秀白玉般的脸上。几只小鱼在石缝里追逐嬉戏,看着欢快极了,秀不由得弯下身子,扯一根水草逗弄起它们来。她从小爱下河,只不过花溪谷的水要比这清冽,能发出金属般的“叮咚”声。
她想着,抬头朝终南山的方向望去。那是她的娘家,也许这辈子都回不去的娘家。倔强的父亲,自从她跟了现在的男人,就发誓与她断绝父女关系。
记得还是去年九、十月的样子,几个山外人来收天麻。父亲开了几亩荒地,一年两茬全部套种着天麻。娘在灶前忙活着一大锅糊汤,山里的苞谷生长期长,锅大柴宽,熬出的糊汤味郁黏香,再佐以山里纯正的酸菜,常常是外来客必点。家里好长时间没这么热闹了,秀兴奋起来,跑前跑后着忙活。她显然感受到一双热辣辣的眼睛,那是一个面生的小伙子,大家喊他新平。小伙子二十来岁,长得很是精神。不笑不说话,一看都是个脑子灵光,经过世面的人。
闲谝之际,新平捡地上落下来的核桃给大家砸开吃,他剥一颗给秀。他的眼神让秀有些慌乱,不由得心砰砰乱跳起来。
挨着正房是一孔破窑,储藏着晒干的冬麻。吃完饭,父亲和其他人起身验货过秤,新平帮秀往回拾掇着碗筷道“叔,你知道谁家有五味子和野菊花?想顺车捎一些。
“五味子前一阵子有人收过了,野菊花倒开得正是时候。”
“我想去看一下,看谁能给我带下路?”“秀娃子,带他到南坡看看。”
“嗳,知道了。”秀脆生生应了一声。
路上,他说自己是蓝田人,父亲早年去世,母亲年迈,曾经偷羊被劳教过。不知道为什么,秀并不觉得他是个坏人,反倒这个男人身上,有种特别的东西吸引着她。她从小羡慕花溪谷的水,可以自由流淌去外面的世界。她拼命学习,从小学到初中再上县城的高中,甚至更远的省城,这是她为自己设制的人生轨迹。然而,读到初中毕业,任其哭闹,父亲却不肯再供她。
每逢集日,母亲总要背上腊肉带她去卖。镇上桥头有过往班车停靠。十几分钟的歇息时间,人们蜂拥而下抢购山货。秀很羡慕他们,盼望某一天,也有人带她坐上这辆车,离开这小小的山坳。
而眼前出现的这个男人,满足了她对那个人的全部想象。他的俊朗,他的见多识广,甚至身上隐隐的痞子气,对从小中规中矩的秀来说都是致命的利器。她预感,也希望会和他发生点什么。
秋日的花溪谷开始泛黄,有些腐草的气息。溪边的小径狭长,不能并行。新平走在后面,看秀红色的小衫在眼前跳动,像他心底窜腾的火苗。
拐过一个小山包,眼前骤然开阔,一片金色扑面而来。这是一个天坑地带,坑底堰水成潭,四周坡上,野菊花竞相开放,炫目像一片锦缎。“看,就这儿。”秀兴奋地叫着跑过去。俯下身,沉醉在一片花香里,山里太阳来得晚,此时刚好爬上对面山头,给秀镀上一层美丽的光芒。新平有些冲动,他喜欢这个女子,从看到第一眼。她清澈的眼睛,浑然天成的少女气息,尤其此刻俯身嗅花的模样,他忍不住猛地过去揽她入怀。
秀有些惊愕,但推他的手却如此无力。她无法拒绝这个男人身上的力量,长这么大头一次,她如此渴望被一个男人带入一个崭新的领域,哪怕下一刻万劫不复……
有血,落在花瓣上,染成夺目的红色。
“好美呀,红菊花!”新平摘下一朵。
“送你。”秀有些羞涩。
新平不再说话,只是紧紧抱住了她。
等家人知道,秀已有一个月身孕。父亲有些震怒,他无法理解女儿一向乖巧,怎会做出这么离谱的事。自从儿子到灵宝矿上,娶了当地媳妇,就很少回来。秀在镇上读完初中,他就不愿让她再念下去了。他怕女儿也飞了。他原想在附近给秀找一个好人家,临老还有个指望。况且这个后生,凭一个过来人的直觉,他能感觉到他身上的浮躁和不安分,甚至心底的戾气,他担心这个小伙子不会让秀过上安生日子。
他不愿把女儿交到这样一个人手中。但女儿性格随他,拿定的主意,十头牛也拉不回。在又一次剧烈争吵后,父亲流泪说从此恩断义绝,秀再敢踏这门半步,他立马撞死崖上。
秀走了,新平就在镇上的小旅馆等她。
二
火烧寨距城南八里,位于峣山脚下,古官道从中穿过,把村子分成东西两边,新平家在路东堎上,是两间破旧的土屋。秀的到来还是引起了村里的一阵骚动,山外的风大太阳高,像秀这样一掐一包水的女人很少见,何况还是嫁到穷得叮当响的新平家。
新平妈佝偻着背,眼睛因为早年熬夜做针线被油灯熏成了烂眼边,牙齿几乎掉光,剩两颗又尖又长的上牙,让她看起来带点凶相。初进门,秀看那牙老是晃动,吃饭碍事,就说不如用线栓着给她拔了,她见娘这样拔过。老人牙根已朽,轻轻顿一下就掉了,娘说过不疼。当她把针线笸箩端到婆婆跟前,新平妈狠狠瞪了她一眼道“少教的东西!”
她搞不懂婆婆为啥不喜欢她,也想不通这样一个冷脸子咋会生出像新平这样的儿子?她曾打趣道“那到底是不是你亲娘?”新平装作生气的样子,狠劲掐她的屁股:“我妈是个苦命人,不许说她,再说小心屁股开花。”虽然是小两口插科打诨的私房话,但听话听音,秀从此再不当他面提婆婆的任何不是。
刚进门的媳妇在婆家总是找不到归属感。新平屁股尖在家呆不住,男人不在时,她喜欢把自己的房门关上,在她心里,这间小屋才是自己的家。屋内陈设简陋,一个连锅炕,一张杂木案板,一口水缸和盛面的瓦瓮,她都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她喜欢看墙上和新平的照片,那是被父亲赶出的当天在镇上照的,那天刚好是她十九岁生日。
“秀,身子这么重还下河,咋不让新平提点井水在屋里洗?”桥上有人喊道。
“没事,婶儿。”她应着,回过神来,看看头顶的太阳,赶忙在水里涮了衣服往回赶。
前日的几场大雨,房屋的山墙有些垮,新平用一根木椽顶着。秀把衣服晾在椽上。今天初一,婆婆一大早赶水陆庵烧头炉香还没回来,新平好像也没回来,案上擀好的面原封未动。她从门口的垛上扯了一笼麦草,扑塌扑塌烧起了火。等锅开始冒气,她出门,对着堎下一间小卖部“新平,新平”地喊起来。小卖部前面卖货,里面支了麻将桌,新平最近跑那个地方有点勤,她叫着叫着就有些生气。“新平,你媳妇儿喊你吃饭哩!”秀听见有人朝里传话,不一会儿,新平小跑着出来,边跑边朝她腆着脸笑,秀扭头进屋。
“饭好了么?一会儿还有事儿呢?”新平边推门边说。“刚才打麻将的时候咋不着急?”秀下着面,满脸不高兴。
“哎呀,看你脸拉得像个烂杏”,男人说着,胳肢她一下。秀“噗嗤”一声笑了,没办法,这男人是她的解药,生再大的气都没用。
饭好了,她先给男人盛一碗,坐灶间看新平囫囵地吃着。窗上的糊纸有些破损,烟和气混浊的光束,落在炕头蓝白格的粗布单子上,秀觉得暖暖的幸福。
“晚上嫑给我留门了,进山拉木头呀。”
秀不吭声,这两年,山林管理趋紧,木头生意并不好做,为了躲避木材检查站,车走的是一辙的小路,碰上雨雪天,那就是拿命换钱。
“没事儿,这次和伟子搭帮,他路子熟。”新平看出秀的心思。
当年新平偷羊被抓,审了三天三夜,愣是没供出开着三轮,在村口接应的伟子。所以伟子虽横,名声不好,对新平却还不错。
“到山里,别忘了打听一下我大我娘。”秀幽幽地说了一句。
三
伟子贩木头已经有一段时间,看得出发了财,用上了大哥大。这次他还带了一个女人,80年代末的中国,一片欣欣向荣,各种舶来品层出不穷,夜总会便是一种。蓝田这个小县城也不例外,每当夜幕降临,各种昏暗蛊惑的灯、男人纵情的嘶吼、女人妖艳的身影,充斥着大街小巷。小翠就是其中一个,女人的领口开得很低,露出深深的乳沟。新平不敢看,秀大着肚子,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沾身了。
老袁的家在沟口,随着卡车熄火的喷气声,院子的狗狂吠起来,屋里的灯也随即亮了。
“可来了,这两天干部挨家挨查呢,吓得我都不敢开门。”老袁边咳嗽边说道,“都饿了吧,要不叫你婶子起来先弄点儿吃的?”
“不了叔,咱还是赶快装车吧,趁天黑!”新平递了一支烟过去。他认识老袁,以前贩天麻的时候打过交道。
老袁拿了手电筒,朝沟里的几户人家走去。不一会儿,他背后跟了三个精壮劳力过来,一百元一车官价,三个人立马行动。先装木料,上面码几麻袋黄豆,最后用彩条布盖好,再用粗绳捆绑结实,一切就绪,新平给老袁数了钱,上车时他终于忍不住问道,“她大她娘还好吗?”
“好啥呀!上坡的时候滚了,现在还下不来炕呢。”
“哦,啥时候让秀回去看看。”
“我看难,那老倔头,”老袁摇摇头“好好过日子吧,你小子,唉!”
“嗯,”他嗫嚅着,下意识朝南坡那个地方看了一眼,月色下,依稀那片菊花依然灿烂。
这次走的是大路,木材检查站的人掀开彩条布的一角,用验粮器朝几个麻袋戳戳,然后绕着车身转了一圈,打开了卡口路障。“怎么样?货上了不一样吧?”伟子朝他挤了挤眼睛。
这一趟收获颇丰,当天晚上,新平没有回去,在车站招待所那间略带潮味的房间里,当他的几百大毛甩过去,小翠立即像无骨的蛇一样缠绕过来,新平沦陷在一种无与伦比的快感里,那是金钱和荷尔蒙碰撞释放出的巨大的快感。
四
秀生了,是个男娃。取名翔翔,孩子满地跑的时候,新平已是当地响当当的人物了。国家实施封山育林,严禁乱砍滥伐,木料黑市基本取缔。新平和伟子合伙开了家赌场,赌场开在村头废弃的砖瓦场里,这里七十年代也曾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,那时候村上没有通电,制坯机还是手动的,父亲是村里唯一能搅动大轮的人。每次送饭,看父亲站在土台上,抡开膀子,拼命扳转大轮,随着大轮的转动,一排排泥坯从模具里刻出,落到传送带上,旁边会有人把泥坯端到板车上拉到机房外晾晒,最后再进窑烧制。力大如牛,能搅动大轮的父亲是村里传奇。但这个烧制砖瓦的汉子,至死也没能住上一砖到顶的瓦房。新平不想和父亲一样,他要给母亲和秀修一座像样的房子。这两个在他生命中同样重要的女人,他能感觉到她们的不和谐,包括母亲对秀的不待见,他心疼却也无奈,母亲一生不易,说多了怕她伤心。他只想着等挣够了钱,盖一座两层楼,母亲楼下秀住楼上,见面少矛盾自然会少些。这年头撑死胆大的,饿死胆小的,等赌场挣了钱,一切都不会太远。
砖瓦场四面野地,离公路也有距离,比较隐蔽。伟子说办赌场,他第一个想到这个地方。事实证明,他的想法是对的,来赌博的人络绎不绝,昔日摆满泥坯的场子,停满了小轿车,不乏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小翠穿梭期间干些端茶送水的活儿,这女人很是活络,他解决不了的事儿,她总能用女人特殊的方式摆平。他知道,这女人喜欢他,时间久了,他也分辨不出是喜欢他的钱还是人,其实也无需分辨,他的心里,只有秀,其他女人的存在,都是他作为雄性动物的本能。想想开春,他手头的钱,就可以盖两层楼了,也算兑了对秀的承诺,他心里有些激动。
五
掰回家的包谷,堆了一地,秀熟练地用铁锥把棒子锥开,用光芯子“唰唰”地褪着,簸箕很快满了,她端到门外的席上去晾。婆婆坐在门外的石头上,怀里抱着翔翔,一边晒着太阳,一边吃着刚馏的热馍。她嚼了一会儿,突然对着孩子的嘴巴喂起来,秀的胃一阵翻江倒海,“妈……你……”,秀嗫嚅着,终于没发出声。她知道,婆婆不待见她。在来新平家之前,她曾天真地以为,天下所有的母亲都像娘一样慈祥。但婆婆对她的冷漠和挑剔,多年来,一如既往,她百思不得其解。她曾以为是块石头也能暖热,但事实不是,做饭一会儿咸了一会儿淡了,下地回来锄头的泥又没刮干净了,出门又不该和谁说什么话了。翔翔两岁断奶她都嫌早了,说新平六七岁还在吃奶,常常她在上面擀着面,新平撩开衣服在下面吃,当妈的长着两个肉奶你不喂孩子当摆设呀?
新平已经很久没回来了,最近她老想山里和父母的那座小屋,那么温暖。其实许多时候,她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。村里关于新平的风言风语她不敢相信,也不想相信。作为一个外乡人,她举目无亲,用蹩脚的关中话和人交流,她学会了关中农村割麦扬场扶犁打耙所有的活路,但仍得不到婆婆待见,她想喊,想跑,甚至恨那个把两个本毫不相干的女人聚到一个檐下,任其弱肉强食的男人。有时她也会傻傻地对着墙笑,仿佛娘就在跟前,问自己说,“秀娃子,冷不冷?”“娘,冷,好冷,这山外的风。”
太阳落山了,婆婆拉了翔翔回屋。说实话,她最近感觉这个媳妇儿有点儿怪。总是颠三倒四,丢东拉西。看人的眼神怪怪的。但她不想告诉儿子,儿子现在是干大事儿的人,她不想让他分心。况且,她不喜欢这个山里媳妇,虽然模样俊点,但又有什么用呢?农村人过日子讲究实在。她这一生,男人死的早,一个人拉扯新平长大,她深深体会到在农村,有势比有钱更重要,她想攀一个人多势众的亲家,多少给儿子一点帮衬。其实她一直惦记队长家的慧玲,他家三个男娃,慧玲最小,虽然长得黑些,但屋里屋外一把好手。那段时间,她正思忖找谁提亲合适,新平却带回这样一个山里媳妇,把她的计划全部打乱。她看得出儿子对这个女人是真好,虽然这两年在家待得时间少些,但耳环、项链、衣服给买得停停当当,而对这个辛辛苦苦把他养大的妈,却疏远好多,对眼前的这个女人她多少有些怨妒,也时常会撒一些气在她身上。
不过这女人肚子还算争气,给她生了个大孙子,那机灵劲儿简直是新平的翻版,孙子是家里另一辈人,比起儿子她愈发疼爱。秀经常下地,翔翔和自己吃睡,自然也和她亲些。她每次喊秀干活,孙子也跟着“秀,秀”地叫,她无端地高兴。感觉还是孙子好,不像儿子,有了媳妇忘了娘。
晌午的时候,新平急头半脑地回来了。“钱呢,给我,我要去银行存一下。”“啥钱?”秀有些懵。“上次给你的三万块钱呀!用牛皮纸包着的。”秀使劲揉搓着前额,极力捕捉着某些记忆。突然,她用手指了指炕洞,新平有些愕然,伸长了胳膊朝炕洞里扒着,灶堂舔过来的火苗已经把钱烧去了一半,他有些踉跄,眼前一片乌黑。这可是他起早贪黑担惊受怕挣的血汗钱,再攒一阵儿,开春就可以盖楼了。他的血直往上涌,一巴掌搧在她脸上,又一脚踹过去“畜生!”他吼着。女人的头,重重磕在了案板上,血顺着发丝滴落,模糊了她的视线,鲜红的,像极了那年花瓣上的血珠子。妈妈的眼泪、父亲的训斥、婆婆的讥笑、村里人的闲言碎语还有新平英俊的脸,不停在她眼前变幻。而眼前这个狰狞的男人,是个坏人,趁新平不在的时候跑过来欺负他,她恨他,顺手抓起菜刀,朝他扔了过去。新平头猛地一偏,菜刀劈进旁边柱子里,他有些惊愕,但容不得多想,当务之急,是赶快到银行把仅存的残币兑出来。“妈,你看下秀,我有事先走了。”他边往出跑边朝母亲屋里喊了一声。秀追赶出来,看新平三步并作两步上了一辆昌河车,驾驶室里,一个脸搽得生白的女人,用血红的嘴,朝他的脸嘬了一口,像青面獠牙的恶鬼。“啊——”她尖叫起来,那叫声,久久回荡在火烧寨的上空。
秀疯了。
秀咋会疯呢?新平百思不得其解。会不会是磕的那一下把脑袋磕坏了?但医生说脑部没有外伤。秀总是乱跑,还捡拾渠道的垃圾吃。他带她医院,却越来越严重。医生说药不能停,不要受刺激,时间长了说不定会好起来。
赌场的生意还得做,秀看病要花钱,母亲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,翔翔眼看着就要上学了。他心里极度苦闷,也只有当花花绿绿的钞票涌向他时,才会得到些许的安慰。
六
新平妈的背越来越驼了,倾起头走路的样子,像极了一只骆驼,翔翔淘得很,吃饭得寻半个村子。堎上地势高,打不出井,吃水得到堎下的人家去担。秀好的时候水缸总担得满满的。现在,她拎一桶水摇摇晃晃回来就成了半桶。此刻,她不由得念起秀的各种好来。但现在想这些又有什么用呢?她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。门外的皂荚树洞是秀的新家,摆满了她捡回的各种垃圾。她总是“嘿嘿”笑着,脸抹得黢黑,因为药物副作用变得浮肿,早已看不出昨日的模样。最可怕的是,这个女人经常衣衫不整就跑出去,这要是让哪个男人占了便宜,新平可怎么在村里活人呀?“唉,我的命咋这么苦呢?整天满村不是找孙子就是找媳妇。要跑就跑远点儿,省得我找。”新平妈抹着泪,一个念头一闪而过,不禁打了个激灵。“也算给这鬼逃条活命吧!”她宽慰自己,朝二嫂家走去。二嫂是河南人,早年逃荒到关中,被门里拉脚的二哥带回,她一辈子没有生养,靠给人牵线说媒挣钱。
“这我可不敢,你新平那歪怂,知道了还不把我吃哩。”二嫂连连摆手。“新平又不常回来,再说秀这病总是乱跑,给他说跑丢了他能咋。”看二嫂有些犹豫,新平妈趁热打铁“离娘钱分你一半咋样?”“那可说好了,这事千万不能让你新平知道,不然我就活不成哩。”“那当然,要送就送远点,免得过一阵儿又跑回来了。”
一个月后的夜晚,秀被人从后梁上接走了,说是去看父母,秀兴奋地拿走了她所有的东西,包括树洞里全部的垃圾。
秀丢了,新平发疯似地找,他找遍了十里八乡的村村落落,沟沟壑壑。但几个月下来,却杳无音信。他彻底被抽空了。他不明白,老天爷为什么这么不公平?这么多年,他拼命努力,就是想给秀一个像样的家,但秀却离他越来越远,这次终于彻底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了。只有他知道自己是多么爱秀,只要给他时间,再一点点时间,他就能给秀宽敞的房子,他原以为,秀会懂他。他原以为,秀那么爱他,不管他走多远,多久,她都会在家里等他。可,不是!为什么不是?他对着空落落的房子大喊。翔翔,是秀在这屋里唯一留下的痕迹,却在偷了奶奶五百块钱后再也没有回来。母亲像变了个人,整天一句话也不说。那个曾经温馨的小屋,像冷冰冰的坟墓。
麻将是个好东西,他甚至有时候想,之所以叫麻将,可能有麻痹神经的意思在里头。开赌场的人上赌桌是大忌,但他一屁股上去谁也别想换他下来。他喜欢方城中运筹帷幄,游刃有余的感觉。喜欢赢一堆钞票再把它输回去,那些玩意儿他曾拼命想得到,现在除了赌桌,他竟找不到它们的安放之处。他不眠不休,酣战了三天三夜,终于一头栽倒在牌桌上。
七
出院后的新平右边变得僵硬,也没了语言功能。他有时也会像个圆规一样,画着圈儿慢慢挪到小卖部门口坐坐。“新平,来摸一把”有人和他开着玩笑。他笑笑,用下巴指指僵硬的右手。“么彩的,右手废了再用左手刨么”那人继续揶揄着。他不再说话,怔怔看着渠道里,秀疯的时候,经常在那儿捡食垃圾,他期盼她的身影能突然出现,哪怕是疯了的样子。
新平妈七十三岁那年走了,都说老人七十三、八十四是门槛。她疲惫的身体,终究无法跨越这巨形的门槛。她走后好长一段时间,人们都在谈论这个也算享受过父子两代荣光的女人。新平还是会坐在商店门口的石头上,看有人上县便“哇哇”乱叫,比划着让买点馍馍之类的回来,他会泡水吃上好几天。下来一连几日,都不见新平出来,人们撞开了门,发现他蜷在炕上,身子早已僵硬。
多少年以后,两个操着河南口音的人来到村里,男人腿瘸,女人一点点搀着上了场堎,在一棵皂荚树下,男人停下,注视着女人用钥匙打开一扇破旧的黑漆木门,屋内陈设依旧,已破败不堪。屋顶透着天光,墙角的蛛网,布满陈年的麦壳和几只风干的蜘蛛。
炕上,她亲手绣的鸳鸯枕还在,她拿起来,拍打上面的灰尘,赫然,一枝菊花从枕中掉落,那是一枝野菊花,她认得花瓣上猩红的颜色,虽已经年,却美如初见。“新平——”她仰天长嘶一声,梁上一只乌鸦惊骤而起,抖落一阵尘土。作者简介
张晓凝,年生,陕西蓝田人,现居西安。喜欢文学,敬畏文字,一直想用文学在这平凡的生活中寻找一方自已的净土,并为之耕耘付出!猜您喜欢往精选▼?肖云儒老师为“陕西文谭”题写刊名●百期感言
?拜访著名作家贾平凹散记
?名家●贾平凹:正善之人——在《黄土高原上的银铃——人民艺术家贠恩凤》新书发布会上的讲话
?渭南小说界第一百期——著名作家弋舟鲁奖作品《出警》研讨会纪实
?《北京文学》发表林喜乐中篇小说《佛珠》
?名家创作谈
冯积岐:追求短篇小说的复杂性和内涵性
?党益民《石羊里的西夏》艺术实验论析●李险峰
?名家●王琪玖散文讲座:曲径通幽法
?李红:文学是一座山——读陕籍著名作家王蓬长篇小说《山祭》有感
?李印功《平凹与三毛》:一个传奇故事的再生——且听编剧东篱一席谈
?安保仁:美哉斯文壮哉斯人——当祖国需要的时候
?频阳子:河边(小说)
?孙见喜:中西医对擂的三件趣事
?李文君:看破不说
?李培战:“非常规”的赵季平
出品单位:陕西文谭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编网络支持:陕西文谭网文谭ID:sxwtw预览时标签不可点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tiweixingnaoquexue.com/nxdf/472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