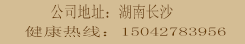![]() 当前位置: 体位性脑缺血 > 脑多发缺血灶 > 在巴厘岛过春节,母亲因为车祸住进了ICU
当前位置: 体位性脑缺血 > 脑多发缺血灶 > 在巴厘岛过春节,母亲因为车祸住进了ICU

![]() 当前位置: 体位性脑缺血 > 脑多发缺血灶 > 在巴厘岛过春节,母亲因为车祸住进了ICU
当前位置: 体位性脑缺血 > 脑多发缺血灶 > 在巴厘岛过春节,母亲因为车祸住进了ICU
原创阿狸三明治
文|阿狸
编辑|胖粒
“她说什么?”妈妈手伸到床外,拉了我一下。
“护士说要让我们转到ICU去。”我低头对她说,“估计今晚没法回酒店了。”
几小时前妈妈发生了一场车祸。摩托车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,妈妈被拽着拖了2米,撞到路旁的木头桌角上,摔倒了。
年的春节假期,我带着妈妈去了巴厘岛度假,顺便可以庆祝她的55岁生日。这是姥姥去世的第一个春节。此前的每年除夕,妈妈都会张罗家人一起吃饭,拍照。北京的年夜饭预订很紧俏,她总是提前2-3个月就告诉我她已经订好了某某餐厅。这个春节妈妈说想要离开北京,避免过于睹物思情。
妈妈是一名医生。医生有个特点,他们能在第一时间想到最坏的结果,但在别人都想要放弃的时候还在坚持努力。自从姥姥病重以来,一直都是妈妈亲手照料。糖尿病的多种并发症严重影响了姥姥的生活质量,病痛也让姥姥的脾气变得越发顽固。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,她既是私人医生,又是护士,是经验丰富的护工,同时也是患者的女儿。她在家里给姥姥买了一个ICU才有电动病床,可以遥控翻身。白天她不在家的时候会请保姆帮姥姥翻身、按摩,晚上她下班回家了就自己给姥姥做护理,测血糖,观察身体的活动情况,调整用药,变化饮食。
但老年人的慢性病是无法痊愈的,很多时候因为生活质量的下降,患者自己都想要放弃了,而且无论治疗与否,最终结果都会一步步恶化——医生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延缓恶化的进程,是所谓的“偶尔治愈,常常缓解,总是安慰”,妈妈几十年在老年科室,对这句话很清楚。姥姥的糖尿病足溃烂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,其他脏器也在日益衰退。姥姥的足溃烂到脚趾发黑,最终露出了骨头,妈妈再也没必要给那个脚趾上药了。她把姥姥脚上的被子重新改好,就去配药了。几天后,姥姥离开了。
我们到达巴厘岛的当天就发现这里的交通非常混乱,双向车道上经常能塞4排车。因为开车太堵,摩托车成了当地人和游客很重要的出行工具,这其中也不乏从没骑过车的新手。旅游城市的摩托车租赁大多是不看驾照的,交了钱戴上头盔就能骑走。医院的两周时间里,急诊室下午最常见的就是绑着纱布,打着石膏的游客。
01
事故
事故发生在除夕当天下午。在被摩托车拖倒之后,很快妈妈就自己站起来了。没有外伤、没有流血,只是撞在桌角的腹部有一些淤青。在路旁稍坐了一下,她就说没事了,回酒店观察一下吧。她是医生,她说没事我就放心了。把妈妈送回酒店躺下后,我出去处理交通事故。今天除夕夜,晚上一定得让妈妈吃点好的补一补。
妈妈的身体要好于同龄人。像所有的医生一样,她能站一整天并且不吃不喝。大学时候她是连续四年的短跑冠军,还进过省游泳队,她的心肺能力尤其好,跟腱也很长。舅舅曾不止一次跟我说:你妈妈穿着“片儿鞋”就能把穿钉子鞋卫冕冠军甩出去十几米(片儿鞋,可能就是布鞋吧),神情骄傲得像是在跟我讲一个传奇。即使是现在,我逛街也从来逛不过她。她也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衰老。
在那之前我没听说过“内出血”,不知道表面不流血,还存在内脏破裂出血的可能。很多人就是因为内出血失血过多又没有及时发现才丧命的。我处理完交通事故后回到酒店,妈妈从床上起来给我开了门。我问她,你现在觉得好点了吗?我想,如果稍微好些了我们就出去吃年夜饭。她还没回答,两眼直直地看向一侧,显得有些迷茫,突然身子就歪向墙壁倒了下去,眼睛也闭上了。我以为,是死神来了。
这个短暂性昏迷是由于突然起身开门造成血压不足导致的。事后理性地分析回想,晕倒可能只有2-3秒钟。她恢复了意识,她跟我说,可能是脾破裂了,我得再观察一下。
您可别再观察了。我通过酒店叫来了医生,血压一直在下降,情况很危险,出诊医生叫了救护车。晚上大约6点,我们到了医院BIMC。
02
入院
巴厘岛的交通太糟糕了。医院的路只要几公里,我们至少开了1个多小时。时间长到足够我给爸爸打了3个电话,给保险公司打了2个电话,给2个舅舅也打了2个电话。巴厘岛和北京没有时差,和家人说这些的时候,全家都在吃年夜饭。
我坐在救护车的副驾,妈妈躺在后面,身边有2-3个急救人员。随行的医生一直跟她说“不要睡觉”。车内外都很嘈杂,车里的仪器变着调得发警报,车外还有喇叭声、摩托车的排气声,街旁酒吧外放的音乐嗡嗡地震着车窗。我回过头去看她,妈妈好像想要跟我说家里存折和人身险,我刚想开口,车子突然向一侧颠了一下,医生赶紧伸手去扶输液的瓶子——救护车竟然挎上了人行道,旁边的马路已经堵得水泄不通。
到医院几轮检查之后,我们离开急诊进了ICU。护士给她换上了病号服,接上血氧检测的设备。几个月前在姥姥住的ICU里我已经很熟悉这些监测设备了。护士让我翻译给妈妈说需要用导尿管,我有些质疑。我当时的工作语言是英语,日常交流是没什么问题,但医疗方面的词我几乎听不懂更说不出,全靠手机翻译关键词。妈妈问我怎么了,我说护士要给你用导尿管,有这个必要吗?她倒是没有迟疑,说:用吧。
但在我心里是有疑惑的。从到了急诊以后,每过一会儿就会有个护士让我去签账单。救护车、CT、超声、输液,这些费用我都能理解,但在我认知中,住ICU、上导尿管,都是姥姥在病危时候才上的手段。妈妈现在看起来很清醒,我担心她是身体虚弱懒得和人争辩,有些任人宰割。但护士也不打算多解释什么,就说是医生要求用的。
护士走后妈妈几乎很快就睡过去,我一整夜没法闭眼。起初我很执着地在等CT报告,做护士的小舅妈在电话里告诉我“CT如果没事就没事了”。但晚上8点就做完的CT到凌晨2点了,他们依然跟我说医生们“还在讨论结果”。后来妈妈说应该是当晚找不到可以接手术的医生,所以一直拖着。她没有跟我说,她看了第一轮检查结果就知道肯定是要做手术了:进ICU,用导尿管,这些都是术前的准备。
夜里3点多我再问CT结果的时候,我终于也感觉出今晚他们是不会告诉我了。我决定去买点东西吃,护士跟我说我马路对面有一个24小时的便利店。医院,赤道雨林气候的闷热和潮湿扑到我身上,我才发现我手脚冰凉得有些麻木。
夜里3点的马路基本上没有什么路灯,有一辆车没开车灯就从我身边呼啸而过,我打起精神穿过这条街。海边度假城市的夜晚很热闹,远远的有海浪声,路上还就地坐着一排刚在酒吧喝醉的游客,看起来玩得很high。巴厘岛人对中国的游客很友好,结账时候便利店的老板跟我说“春节快乐”(happyChinesenewyear)——他不说我都快忘了。
这间ICU病房像是临时用玻璃在走廊拐角搭建的,一张床,两边是刚刚拉进来的监测设备,墙上有3个插销,还有护士特意给我搬进来的一把折叠椅。医院里常看到医护人员在走廊里小跑,这间ICU是正对着护士站的,护士走进来只需要5步路。这么拥挤的距离让人有些安全感。回到病房的那张折叠椅上,我吃了2包士力架,查了一会有关医疗的信息后,就盯着血氧仪发呆了。多条未读的拜年信息,我一条也没敢回。
护士再进来的时候,已经是凌晨5点左右了,她跟我说,8点会做手术。把妈妈叫醒之后,她让我问问有没有可能做微创手术。妈妈一直保持着运动员身材,小腹很平坦,之前的腰围一直是1尺8,更年期后也不过刚刚2尺。她醒来之后显得有些精神了,跟我说:“如果能做微创手术的话,以后穿比基尼也看不出伤口的。”说着说着竟然笑了出来。
03
手术
巴厘岛的医生和护士是很好分辨的。除了服装以外,体型上有很明显的差别。护士,和我们这几天看到的司机、小贩、服务员前台一样,都是很黑黑瘦瘦的;医院里的急诊大夫和住院医生,和机场的签证官员一样,明显都要更胖一些。反观我国的医生,好像都瘦得像理发师似的,高强度的外科医生就更是如此了。
7点钟,给妈妈主刀手术的外科医生来了,是一个比住院医生更胖的胖哥。胖哥医生的肚子至少超出腰带5cm,我看着他,突然有些嫉妒:要是妈妈也有这样的肚子,厚厚的脂肪层也能让她这次少受点伤,说不定根本用不着手术。妈妈也同意我的歪理,今年她腰围已经长到2尺2了,以前所有的衣服都要淘汰了——但终于能买新衣服了。
胖哥医生说不能做微创手术,必须要剖腹才行。妈妈撅了噘嘴,过了一会可能觉得是我没跟医生表达清楚,就又让我确认了一遍是不是一定要剖腹。胖哥医生开始一条条讲手术麻醉的风险,手术风险的知情同意书上至少50%的单词我都不认识,但我还是很快就签字了。这是一场毫无准备的赌博。医院、不能通过查资料去选择主刀医生、不能在术前了解手术方案。小时候妈妈没什么时间给我做饭,会跟我说“有什么就吃什么吧”。我没有什么主观能动性,能做的基本只剩祈祷了。
上麻醉前,妈妈冲我笑了一下。很快,她心率就飙升到,心率警报器像是要喊破了嗓子,几个医生几乎手忙脚乱地把她推出ICU,跑着向手术室去了。手术室的门关上,“正在手术”的指示牌亮了起来。我的工作暂时结束了,我想我必须要赶紧睡一觉。爸爸跟我说,手术后的48小时也很重要,如果造成术后感染,往往还需要再次剖开肚子,那样就更危险了。
医院很小,医院都要小很多。医院一共只有2层,1层是急诊和门诊,还有药房。每天下午1楼都会坐满出车祸的、被蚊虫或者海蜇叮咬中毒的,在海上冲浪受伤的、还有腹泻的患者。住在巴厘岛的度假别墅时,谁都会觉得巴厘岛是度假天堂,医院像是天堂的背面,又冷又昏暗,竖起耳朵的话还能经常能听到哀嚎声。2楼是手术室,有2间ICU病房和3-4个常规病房。2楼人不多,相对安静不少。
手术室外面有一排地铁同款的硬座,3个相连的塑料座椅都是空着的。我也懒得管什么形象了,就决定横躺在那个椅子上,枕着自己的胳膊,先是哭了一会儿,然后就睡着了。医院后把我叫醒的。
爸爸和大舅出国都不方便,家里有护照能随时出国的就是小舅舅。小舅舅是海员,常年飘在海上,春节期间是航运高峰,往往很难回国过年。那年因为姥姥去世,这是他好几年以来第一次在国内和舅妈表妹一起过春节,结果连一顿年夜饭也没吃安稳。除夕夜里,他买了北京直飞巴厘岛的航班。
妈妈躺在ICU里面还没有从麻醉中醒来。舅舅说,走吧,去吃个午饭吧。我上一次吃饭,是昨天中午,那时我和妈妈刚冲浪回来,在酒店吃的大虾沙拉。医院,手术就结束了。
妈妈的职业塑造了她的性格。她的性格又塑造了我。长期的医生职业训练造就了她强大的抗压能力和一种隐忍的力量,她几乎很少展现出焦虑或者手足无措。
我一直很崇拜作为医生的母亲。有很多次在火车上、在飞机上有旅客突然病倒,她都是在听到广播后第一时间去到患者身边,好像这是一种义务。长大后妈妈也会在闲聊时和我讲很多他们也无能为力的患者,她所在的神经内科(脑内科)属于老年科室,很少有出院时能活蹦乱跳走出病房的患者。医院时已经风雨飘摇了,医生能做的实质性改变其实不大,但他们依然会全力以赴去做尽可能多地抢救,在想到最坏的结局情况下仍然全力争取一丝希望。而我们大部分人的工作缺乏这种在黑暗中争取曙光的精神和动力,毕竟我们手上一个“项目”做坏了也不会出人命,一篇稿子写的不用心,也至于在道德上谴责自己。
妈妈对待自己的生活也是如此。她总是想着如何去解决问题,改善现状,她的乐观不是无知带来的乐观,她看到了危险,承受着压力,但她传达给我的是希望和信心。妈妈是在北京的部队大院长大的,思考问题时常带着大院孩子特有的幽默,面对困境时也常常跳出来自我调侃。
我们刚刚到巴厘岛的时候,妈妈显得很兴奋。在逛街时,她一时兴起去做了一头脏辫。那时候我发了条朋友圈,笑称她是黑人女子运动员。在病床上她多次说道,这一头脏辫真是物尽其用啊,要不然这2个礼拜不能洗头真的会很难受呢!说完她总会一脸得意,自己把自己逗得很开心。
刚到巴厘岛以后编了一头脏辫vs因为手术将近2个礼拜没能洗头,脏辫真是物有所值
从高中开始,我常觉得妈妈更像是我的好朋友。我们会在吃饭的时候讨论一天的见闻,她很少把我当成孩子,会跟还在读高中的我讲很多她工作中遇到的烦心事。但她也会独自承担现实的压力,让我生活在她尽力维持的温室中,即使家庭遇到变故,我也从没有觉得生活是窘迫的,是提心吊胆的。
坚定和温柔是她给我的精神力量。如果我做的不好,她也很少骂我,她总是说她相信我,只要肯去做就会有结果。我一直凭着“希望”去做事:我相信努力去做的事情最终都会向着理想的结果更靠近一些。这种希望,就是她给我的温柔的力量,让我全力去做好我手上的事情。
04
术后
手术进展得很顺利,主刀的胖哥医生见到我显得有些兴奋。他拍了好几张剖腹时手术的照片,在手机上津津有味地给我讲解:啊,你看,脾脏完全没问题,胃的前后都有穿孔,但我都已经给缝合好了,胰腺的尾部撞坏了,我只能给它切下来了,就在这个盘子里,你要不要看看?从她的腹腔里面取出来2升的积血,所以我们要给她输血,她昏迷的时间可能也要长一些,不过今天晚上或者夜里应该能醒过来。配合着手机翻译,终于给我讲明白了,他看起来很高兴。国外的医生碰上大手术的机会要比国内的医生少很多,医院基本上都是游客,一年能轮上几个大手术是很难得的,胖哥医生当然会开心了。
主刀胖哥在Google下载了肝脏和胃的示意图,给我讲解他都做了什么。
手术是差不多中午11点结束的。到了晚上8点,妈妈还没有清醒过来。我坐在床边看她,感到一阵陌生,是一种我只在姥姥病重时看到过的虚弱和疲惫。妈妈和大舅舅长得像姥爷,是面颊消瘦,颧骨突出的巴中川渝人长相。家里只有小舅舅长得像姥姥,她是江南美人,面颊十分饱满,眼睛也大大的。躺在ICU病床上妈妈,脸色发暗,双眼紧闭,唇色缺血发灰,身上插着输氧管、鼻饲管、导尿管,手上插着静脉滞留针,身边挂着许多检测机器。原本妈妈和姥姥长得几乎不像的,但此刻她和几个月之前躺在ICU的姥姥一模一样,只是更瘦了不少。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她的虚弱和衰老。
小时候有一次家里进来了一只巨大的黄蜂,我那时从来没见过黄蜂,吓得一动不敢动,妈妈当时在洗碗,手上有很多泡沫,她就指挥我,开窗,用报纸把黄蜂赶了出去。就像这次,我们一起赶走了突然到访的死神。她用她的冷静安慰着我,让我可以按部就班去做一项项术前术后的工作。守床的时候我想起《冰与火之歌》里面一句话,“面对死神,我们只对它说一句话:nottoday”。
术后的恢复很顺利。妈妈出事当天只吃了些沙拉,胃里很干净,即使胃壁被撞破了也没有什么油腻的食物残渣流到肚子里,避免了很多术后感染的风险,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。“很幸运”、“幸亏”,她躺在床上的时候经常说起这些觉得幸运的地方。
离开ICU的第一天,是妈妈的55岁生日。次日,医生帮她把鼻饲管拿掉,一周以来她终于可以吃一点流质食物了,类似于粥或麦片。虽然可以吃饭了,但我仍然觉得有些难过,毕竟我本来的计划是在她55岁那天一起吃海鲜大餐,因为她最爱吃海鲜。但她很高兴,她说她其实最爱喝粥,让我管护士再去要一碗。
作者后记
文中没有来得及去写,很感谢巴厘岛医院看我们2次,还帮我们协调了回程机票改签的事情。自从事故发生以来,我一直想找机会把它写下来,但前两年每每回想起来仍然感到恐惧,像是有一只恶手伸出来攥住我的心。后来我想再不写下来就该忘了,所以很感谢通过三明治写故事这个契机能把它记录下来!妈妈常说这次事故之后让她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了,玩得时候要“悠着点”,不过她身体恢复得很好,第二年她就跟着单位一起去瑞士爬雪山了,还是那个运动健将!如果说我学到了什么,可能就是出门旅游一定要买保险!!!而且要仔细看清保险赔付条件,不要买那种赔付金额大得夸张但只在身故时才赔付的保险,买的保险一定要涵盖当地医疗费用才行。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tiweixingnaoquexue.com/nxdf/9685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