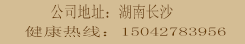![]() 当前位置: 体位性脑缺血 > 脑缺血模型 > ldquo入职季青年学人rdqu
当前位置: 体位性脑缺血 > 脑缺血模型 > ldquo入职季青年学人rdqu

![]() 当前位置: 体位性脑缺血 > 脑缺血模型 > ldquo入职季青年学人rdqu
当前位置: 体位性脑缺血 > 脑缺血模型 > ldquo入职季青年学人rdqu
“外省人”的文学命运[1]
——重回《二月杏》创作前后兼及八十年代初的文学氛围
谢尚发
(原载于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年第8期)
内容提要:梳理相关资料可以看出,贾平凹既没有典型的知青经历与伤痛,也对地质勘探生活不甚了解,却在年发表了以此二者为题材的《二月杏》。这与他年年初到北京领奖所经历的伤痕文学刺激,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。但这部作品发表后不久就遭到了批判,欠缺生活经验、消极灰色的思想调子、反映现实的不准确等成了批判的点。这彰显了年代初文学局势的多变、文学中心与地方的信息落差等诸多文学史的观察点。
关键词:《二月杏》八十年代文学氛围外省人
“文学与时代”是文学研究中较为普遍的话题。“时代”又往往被具体化为文学制度、文学批评、评奖、稿酬、文学消费等,尤其从“文学的规训与惩罚”这一点上来说,容易造成一种趋势、潮流和氛围,无形中或隐或显、或多或少地对作家的创作带来各种各样的刺激、牵引等,往往凸显为型塑文学的重要力量。但一俟落实到具体的作家身上,则千人千面,时代的变革与境况也千差万别,人与时代之间、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都成为可资梳理的线索,从中窥见作家创作与时代氛围之间的调配、磨合与守衡。虽然这一“时代氛围”[2]始终以外在要素的面貌出现,但它从外在所施加的作用力,往往能于作家的内在心理引起较大波澜,推动着他们前行,才会有作家创作的“分期”,以及文学史的“历史时期”的形成。尤其是一个作家、刊物、机构等处于初创期的时候,这种机制的作用就更加明显。“文学的时代氛围”在雕琢、促成文学行动者定型的过程中,力量的大小与作家、刊物和机构等的发展历史是成反比例关系的。这在贾平凹的创作中,尤其是80年代早期的文学生涯中,表现极为明显。围绕在《二月杏》写作前后所纠缠着的各种“文学的时代氛围”及其构成要素,以潜移默化或暴风骤雨等各种形式,影响着贾平凹的创作抉择。因此,通过勘察围绕着作家的创作、发表和阅读等时代的力量,从而透析其对文学的影响,不失为解读作家转型、创作风格转变、文学史丰富侧面等的有效途径之一。
一、家乡来了地质队
年的某一天,贾平凹接到一个吉林人民出版社编辑的电话,约请他写一部关于“知青”的作品,作为他们丛书的一部分。这一约请,让曾有过“知青”经历的贾平凹感慨万千,他在后来所写的这部作品中,带着浓重的感情叙述道:“说来真是奇怪,距离了知青生活二十五年,二十五年里每每作想了五年的岁月莫不是咬牙切齿地诅咒,而现在却变得那样的亲切和珍贵。”[3]按照贾平凹的交代,他是年初中毕业后,随即成为“返乡”知青的。15岁的贾平凹先是过了一段四处大串联、参加批斗老师等活动,被宣布毕业后,回到家中无所事事,随即很快在父亲的严厉批评中,安心地在老家丹凤县棣花镇当起了“农民”,这也成为他把作品命名为“我是农民”的原因。但当时,对于贾平凹而言,他的身份是尴尬的——“回到了棣花,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,在农民里又居于知识青年。”[4]稍作反思,贾平凹立即认识到,自己的身份从来都不曾是“知青”,从出身和当时的经历而言,他这个“返乡”而非是“下乡”的初中一年级毕业生,虽然头上顶着“知青”的帽子,却着实是地地道道的“农民”——“我的家却原本在乡下,不是来当农民,而是本来就是农民。”[5]因此,一本原本被邀约写“知青”主题的书,结果被贾平凹写成了“农民”。披阅这本书前后的文字可以看出,贾平凹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“知青”,自己回到老家棣花镇参加农业生产活动,也不是“上山下乡”,而是作为一个农民的本分行为。也正是从“农民”,且是一个“年轻的农民”出发,贾平凹对那些真正从城里下放的“知青”充满了“怨和恨”。
在我的经历中,我那时是多么羡慕着从城里来的知青啊!他们敲锣打鼓地来,有人领着队来;他们从事着村里重要而往往是轻松的工作,比如赤脚医生、代课老师、拖拉机手、记工员、文艺宣传队员;他们有固定的中等偏上的口粮定额,可以定期回城,带来收音机、书、手电筒、万金油,还有饼干和水果糖。他们穿西裤,脖子上挂口罩,有尼龙袜子和帆布裤带,见识多,口才又好,敢偷鸡摸狗,敢几个人围着打我们一个。更丧人志气的是他们吸引了村里漂亮的姑娘,姑娘们在首先选择了他们之后才能轮到来选择我们。……我心里厌恶着小白脸的浅薄。他们在时代中落难,却来到乡下吃了我们的粮食、蔬菜和鸡,夺走了我们的爱情,使原本荒凉的农村越发荒凉了。[6]
贾平凹的这些叙述,既有夸大其词的嫌疑,也有事实的成分。据相关记载,“商洛的知青运动,伴随着全国的形势发展变化,亦步亦趋,紧张有序地推进,但其规模和影响远没有其他一些地方大。参加知青运动的学生中,除外地分来的几批大学生外,主要以本地初、高中毕业生为主”[7],且前后分来的外地大学生知青相当少,十分分散地被分配在商洛市的一区六县,加上大山阻隔等原因,真正到棣花镇或者棣花镇附近的知青,几乎没有。这种状况和“商洛地处秦岭山区,经济相对落后,城市人口少,城市化水平偏低”[8]有关。以丹凤县的“老三届”为例,插队人数仅仅有35人,但像贾平凹这样回乡的知青人数,却足足有人。即便如此,回乡的知青也受到了高规格的待遇。一位知青记述道:“在北门外东方红广场召开了轰轰烈烈的欢送大会。……在公社院子举行了简单的上山下乡知青欢迎仪式。”[9]敲锣打鼓、横幅标语几乎是这些人的“标配”,热闹场面非凡。相比而言,贾平凹的“知青经历”却暗淡了许多。他说,“我们领取了毕业证,在校园里四处走动,破烂不堪的校舍使我们产生了破坏的邪欲”,于是动手打砸,“又左顾右盼,希望能拿些东西带回家去。”[10]他只能眼见别人的热闹的欢送和欢迎仪式,道听途说关于知青的种种“故事”,而自己更像是“遣返回家”的弃子。但从根本上来说,这对于贾平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作为一个农村孩子,毕业回到原来的地方,是农民依旧做农民——他只不过是没能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罢了。那些下乡的知青,的确如贾平凹的记载一样,多数人凭借着知识,当了赤脚医生、代课教师等,而且他们还有相应的工资补贴,经常回城采购生活物资。据丹凤县的相关档案资料记载,程毅飞、王丹叙述到,“自年到年十一年间”,在全县前前后后下放的名知青中,“2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70多人加入了共青团,6人参加了大队领导班子,48人参加了社、队理论骨干队伍,还有8人担任了民办教师、赤脚医生、保管、出纳员等。”[11]这和贾平凹回乡后的落寞遭遇几乎是天上地下。当贾平凹默默跟随家人在田地里劳动、砍柴、工地上干活而没有任何工资补贴的时候,这些知青可能正在以傲人的姿态,吸引着商山丹水边的漂亮女子。从这些数据、文献记载也可以看出,贾平凹既没有知青的典型性经历,实际上也在心理上排斥,甚至反感知青,因此难以理解知青的处境、精神和心理的困顿、他们的遭际以及故事背后的故事等,应该也是事实。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的批判、背叛等,也和他基本无缘——他的“串联经历”也只是到了西安后,“夜里在新城广场排队买毛主席纪念章”;他的批斗,也是夹杂在同学们的批斗中间的,还直言他“没有整过王老师”[12]。对于他而言,忏悔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,并进而要在自我折磨中来达到救赎的目的,说来也是矫情和虚伪的。
贾平凹的老家棣花镇,位于秦岭南麓,绵延的大山和山谷间的河流与河谷平地,是这里常见的地理风貌。按照地理地貌的划分,整个商洛市又呈现出三分的态势来:商州区及附近,“山地占优势,是一个‘八山一水一分田’的山区。东部地势较开阔,宽谷和梁塬占的比例较大,也只是‘七山一水二分田’的地区。西部镇柞地区,山大沟深,河谷川地很狭小,表现出‘九山半水半分田’的特点。从土地利用看,耕地所占比重小”[13],当地居民主要依靠山货如核桃、柿子、木耳、山茱萸、麝香、天麻、桔梗等[14],作为经济来源的重要构成部分。因为山多,商洛地区自然也就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,稀有金属资源“铌、钽、锂、铍、钇等”,金属矿产“铁、铜、铅、锌、钨、汞、锑、铬、锰、银等20余种”,以及非金属矿藏“煤、石棉、云母、重晶石、萤石、大理石、石灰石、磷块岩、黄铁矿等”[15],矿产勘探以及开发,遂成为此地较为频繁的活动。具体到丹凤县,矿藏的勘探和开发则主要集中在铜矿上,尤其是“蔡川乡皇台铜矿,唐宋以来朝廷多次”[16]开采以铸铜钱。但观察相关统计数据,贾平凹的老家棣花镇基本上没有探明矿藏储量丰富的地质资源,矿藏比较丰富的蔡川乡、北赵川镇、留仙坪乡等距离棣花镇也较远。当然,据相关陕西省的地方志记载,—年间,陕西省冶金、地质系统“为寻找铁铜矿,先后勘查柞水大西沟、韩城阳山庄、洋县毕机沟、太白王家楞等16处铁矿,及宁强刘家坪、丹凤皇台、山阳下官坊、镇安二台子、柞水冷水沟等8处铜矿,投入钻探19万米,探明工业矿床5处。”[17]同样的记载,也出现在《商洛地区志》中[18]。这期间,石油勘探、煤矿勘探等工作,也在商洛地区不断地展开。但因为这一地区金属矿藏丰富而石油煤矿等储量较少,以石油和煤矿为主的地质勘探为期较短且几乎不成规模。哪怕棣花镇附近有相应的勘探活动,也应该极少且不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。
自从初中毕业回家务农之后,贾平凹虽然经历了一段消极的时光,但在父亲的批评和严厉管教下,很快意识到应该承担起家庭重担,于是田里田外,家里山中,常能见他的身影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,要跟着堂哥去深山里砍柴售卖,以换取经济来源。在一次干活的歇息空当,坐在地堰上的贾平凹和几个同龄人,饥饿难耐,正想着美食的时候,他叙述说,“却看见远远的那座作废的砖瓦窑里有人影在动。砖瓦窑下是我们村种着的一片菜地,常常被人偷窃。正中午的谁又去那儿偷盗吗?待趴在窑厂后的土塄上一看,地质队的工人和邻村××的老婆在那儿干事哩!那半年里,地质队驻扎在丹江河滩钻井探石油,地质队的工人有钱就勾引村里的妇女。已经有风声传出谁谁谁和工人好了,谁谁谁脚上穿了翻毛皮鞋是靠他老婆挣的。××的老婆光着下身被地质工人抱着抵住了胡基壕沿上,狗女人手里拿着一个烧饼在吃哩!我们嫉恨着那地质工人,更嫉恨着有烧饼吃的女人,一声‘哇’的大喊,又掉头跑开,在村里大肆张扬,说那女人身子被撞着,烧饼也摇着老吃不准,但还是撞毕了,烧饼吃完了。不久就听到消息,××在家里用皮绳抽打他的老婆,而那个地质工人也调走了,走时没有带铺盖。”[19]因为是事后的追忆,自然多多少少会带有一点夸张的成分,但地质勘探队在此地的存在,应该不会是虚构。与此同时,在嫉恨“下乡知青”的同时,他也嫉恨着身边那些“成功”的人士,其中一位便是他看不上眼的竟然当了地质工人的同学。贾平凹叙述说,“不能使我们心理平衡的,倒是长着吹火状嘴的,老流着鼻涕,在人面前抓虱子的那个与我同学过的,他为什么就能去地质队呢?我们一群土著的知青愤愤不平,密谋过、递交过攻击他的意见书,散布过他的种种不是的谣言。”[20]从这些言辞中,也可以看出,自称“返乡知青”的贾平凹,对地质勘探队抱有多么大的“意见”,对他们的愤愤不平应该在心中是根深蒂固的。回到年代的创作中来,可以看出,贾平凹的回乡“知青”经历,和他在回乡的岁月里的所见,此后就成了他写小说时“捕风捉影”的素材。
二、北京之行
在接受谢有顺访谈的时候,贾平凹谈到研究者把他的创作归之为“地域文化派”、“寻根派”、“现代派”或“传统派”等之类的潮流中,“不是很准确,也都不是很重要”。他解释之所以如此说的缘由,是因为身居西安的他,与“潮流”实在是隔得太远。他说,“我一直生活在西安,在西北,这里毕竟不是文化中心,属于外省人,而且没有形成一个文学圈子,基本上是单干式的。……在西安各种交流少,但新东西一旦传过来,起码自己就要独立思考一下,能逼着你想好多东西,你得单独来弄。”[21]“外省人”身份的清醒定位,足见贾平凹既有对自己创作跟不上潮流的自卑,也有对这份落伍的自豪。实际上,在年代初,新时期的文学氛围,的确在北京、上海要更为浓郁,而在边远的大西北,人们还仍旧处在之前的“旧的文学氛围”中。其时,卢新华的《伤痕》和刘心武的《班主任》分别发表于上海和北京,引领了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潮流“伤痕文学”,浩浩荡荡地批判“文革”及其所遗留下的“伤痕”。但从年刚刚走出来的贾平凹,还在西安左冲右突,试图写出自己眼中的“文学新人物”。-年间,贾平凹苦心经营自己的文字,开始从“文革文学”的旧的因袭中试图突围,冲破种种旧有的框架和套版。然而创作仍旧打不开局面,所写作品虽各方出击却依然反应平平。正如他在一篇写作于此时的创作谈中所言及的那样,“在‘四人帮’横行时,……出现了图解、公式、雷同,而今说某一篇作品没意思,恐怕问题也就在这里了。”[22]这促使他反思自己的创作,问题到底出现在了哪里?提到的三个关键词,仍旧是“图解、公式、雷同”,一如其更早的作品《一双袜子》、《深深的脚印》、《弹弓和南瓜的故事》等小说——阶级矛盾、艰苦奋斗、作风传承等,几乎是当时文学作品最主流的思想。恰好,年毕业不久的贾平凹,被工作单位陕西人民出版社派往咸阳市礼泉县烽火大队写社史,碰到了农科站的两位活泼、爽朗的姐妹,“她俩聪明伶俐、爱笑、爱卫生。她们对生活有诗一般的憧憬,对事业有执着的追求,对爱情也有朦朦胧胧的向往。”[23]贾平凹被她们深深地吸引,加之两个本家姐姐和正在热恋的爱人及其闺蜜,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为他提供了书写“新时代、新人物”的契机[24]。没多久,他就拿起笔来写起了《满月儿》,很快便发表于处在新时期文学前沿阵地的《上海文学》年第3期上。贾平凹沿着“旧有的文学惯性”——现实主义创作原则[25],在题材选择、人物塑造和思想表达上所摸索出来的道路,很快获得了全国性的肯定——《满月儿》获得了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[26]。这个全国性的奖项,让贾平凹这个“外省人”一跃而成为全国文坛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tiweixingnaoquexue.com/nxmx/4723.html